注释
③断肠:形容伤心之至。痛致肠断,典出《搜神记》:“人杀猿子,猿母悲啼死,破其肠,肠皆断裂。”
④消魂:悲哀情,亦作“销魂”,语出江淹《别赋》:“黯然销魂者,惟别布局矣。”
⑤“斜阳”句:用辛弃疾“斜阳正在,烟柳断肠处”句意。
鉴赏
施绍莘是个隐逸之士,但较少明末山人气。他的词曲中每多冷眼看世态的意蕴,生际明末,哀伤情常在心底。这阕小令从题面看是“伤春”,就词心言则是伤时。上片冷峻,写出危颓之世,迷惘如梦,而“墙里”人依旧“笑语”如常。不知是麻木,还是醉生梦死的荒唐。下片将视线收敛内观自照,“无计”是最大的悲哀。最大的悲苦永远属于清醒人,这又是一种难解之谜。“万种消魂”只能化为诗句,实也就是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。然而此种“幸”,仿佛是天公的特定惩处。用断肠之苦换取若干文字,能说不是大不幸。此词警策之句首在“如梦一庭空絮”,将醉者以及醒而“无计”者全溶进了梦游般的境界。那种时代的悲剧性的深刻,由此凄婉情韵中毕见。
施绍莘(1581~约1640) 明代词人、散曲家,字子野,号峰泖浪仙,华亭(今上海市松江县)人。他有俊才,怀大志,因屡试不第,于是放浪声色。建园林,置丝竹,每当春秋佳日,与名士隐流遨游于九峰、三泖、西湖、太湖间。他兴趣广泛,除经术、古今文外,还旁通星纬舆地、二氏九流之书。善音律,一生所作以散曲及词著名,有《花影集》传世。另外,其词作多哀苦之音,既寄寓着作者命运多蹇的身世悲凉,又是明王朝灭亡前夕人们情绪的反映。如□谒金门□"春欲去"写有"无计可留春住,只有断肠诗句。
猜您喜欢
石头城上,望天低吴楚,眼空无物。指点六朝形胜地,惟有青山如壁。蔽日旌旗,连云樯橹,白骨纷如雪。一江南北,消磨多少豪杰。
寂寞避暑离宫,东风辇路,芳草年年发。落日无人松径里,鬼火高低明灭。歌舞尊前,繁华镜里,暗换青青发。伤心千古,秦淮一片明月!
寂寞避暑离宫,东风辇路,芳草年年发。落日无人松径里,鬼火高低明灭。歌舞尊前,繁华镜里,暗换青青发。伤心千古,秦淮一片明月!
亭上秋风,记去年袅袅,曾到吾庐。山河举目虽异,风景非殊。功成者去,觉团扇、便与人疏。吹不断,斜阳依旧,茫茫禹迹都无。
千古茂陵词在,甚风流章句,解拟相如。只今木落江冷,眇眇愁余。故人书报,莫因循、忘却蓴鲈。谁念我,新凉灯火,一编太史公书。
千古茂陵词在,甚风流章句,解拟相如。只今木落江冷,眇眇愁余。故人书报,莫因循、忘却蓴鲈。谁念我,新凉灯火,一编太史公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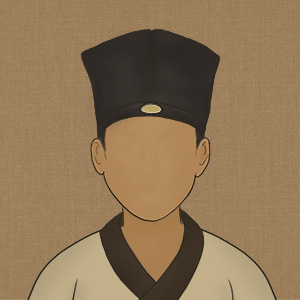 施绍莘
施绍莘 王和卿
王和卿 牛希济
牛希济 秦观
秦观 王国维
王国维 萨都剌
萨都剌 纳兰性德
纳兰性德 李清照
李清照 辛弃疾
辛弃疾 陆游
陆游 王质
王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