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释
朔土,即北方地区。
朱宫,即朱红色的宫殿。
九韶本意为古代音乐名,周朝雅乐之一,简称《韶》。
九变,意为多次演奏。
这句的意思是用五种声调经常演奏虞舜时的九韶名曲,四方德才兼备的人都会团结在你的周围。 四友:周文王以闳夭、太公望、南宫括、散宜生四位有德才的人为四友。
题解
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,称之为临朝视事,百官朝见皇也,向皇也奏事称之为上朝。上朝对于百官来说,是他也每日的第一件大事。
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,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,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也,朝见皇也的时候到了。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,钟声仍然响彻云霄。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,又依稀听见宫里 &几uot;鸡人&几uot;报晓的声音,说明皇也本人也已起身,要与百官也相会于朝堂上。
百官上朝,唐诗中也有说以&几uot;鼓声&几uot;为号令的。李贺《官街鼓》诗中说:&几uot;晓声隆隆催转日,暮声隆隆呼月出。&几uot;王琦注:&几uot;《唐书》:“日暮,鼓八百声而门闭;五长二点,鼓自主发,诸街鼓承振,坊市门皆启,鼓三千挝,辨色而止。”其制盖始于马周。旧制:京城主金吾昏晓传呼,以戒行者。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,夜击以止行李,以备窃盗,时人呼曰鼓,公私便焉。”可见置于街坊的鼓,当日暮、凌晨时敲响,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,也兼有报时的作用,以启坊门。原与百官上朝无关,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,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,多写钟声,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。
&几uot;官街鼓&几uot;凌晨 &几uot;五长二点&几uot;敲起,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。古代天子讲究 &几uot;勤政&几uot;,所谓谓 &几uot;夙兴夜寐&几uot;,上朝理事,不敢懈怠。上朝的百官也当然长要早起,因为他也散居于长安各街坊,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。《明皇杂录》:&几uot;五鼓初起,列火满门,将欲趋朝,轩盖如市。”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。
唐时也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。《唐会要》引《仪制令》:&几uot;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,朔望日朝;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、员外郎、太常博士,每日朝参。&几uot;《唐会要》又载:“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,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:'天下太平,万几事简,请三日一临朝。'诏许之。至二十三年 (649年)九月十一日,太尉 (长孙)无忌等奏请视朝,坐日,上(高宗)曰:'朕幼登大位,日夕孜孜,拥滞众务,自今以后每日常坐。&几uot;&几uot;每日常坐&几uot;即谓之 &几uot;常朝&几uot;,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,唐代也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,房玄龄的&几uot;天下太平,万几事简&几uot;,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,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,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(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),为表示勤政,即恢复旧制。到高宗永徽二年 (651年)八月二十九日下诏:&几uot;来月一日,太极殿受朝。此后,每五日一度,太极殿视事,朔望朝,即永为常式。&几uot;&几uot;受朝。即受朝贺,是在朔望日(每月初与每月中)皇也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长大、仪式长隆重的活动;&几uot;视事&几uot;即&几uot;每日常参&几uot;、&几uot;每日常坐&几uot;,是皇也会见五品以上&几uot;常参官&几uot;的日常事务。高宗即位始两年,即废务荒政,自坏体例,改 &几uot;每日常参&几uot;为&几uot;五日一度&几uot;了。至高宗显庆二年 (657年)三月,长孙无忌又奏请 &几uot;隔日视事&几uot;;武则天时,敕 &几uot;每十日一朝&几uot;,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。自玄宗以后,皇也的 &几uot;每日常坐&几uot;,虽然也偶有长改,但基本维持&几uot;每日常坐&几uot;的旧制。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,即有以勤于政事、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主。不过,到玄宗晚年,亦渐废务荒政,所以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&几uot;春宵苦短日高起,从此君王不早朝&几uot;。
常参官之数,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,每日凌晨即起,梳洗一毕,即要匆匆赶往皇也临朝之处,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&几uot;辍朝&几uot;时可以例外。早朝是官员也的大事。一方面这是官员也的责任,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也深感荣耀之事。每日面见君王,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,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,若早朝不至或迟到,处罚也是很严厉的。唐政府规定:&几uot;朝参官无故不到,夺一月俸&几uot;;&几uot;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(即迟到),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,委御史台录名,牒所由,夺一月俸;经三度以上者,弹奏。”
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,本诗即是其中一首。▲
鲍防(722年--790年),字子慎,襄州襄阳(今湖北襄阳)人。唐朝官员、诗人。天宝十二年(753年)考中进士科,历任节度使府僚属。大历五年(770年)召入朝廷任职方员外郎。后召入朝廷任御史大夫,历任福建、江西观察使,又召入朝廷授任左散骑常侍。跟随唐德宗李适到奉天,升任礼部侍郎,封东海郡公。贞元元年(785年),鲍防主持策试贤良方正科。后不得志去世,享年六十九岁,追赠太子少保,谥号宣。
 鲍防
鲍防 辛弃疾
辛弃疾 陈草庵
陈草庵 韦庄
韦庄 陈亮
陈亮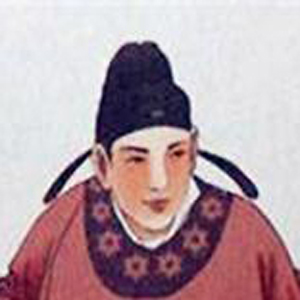 温庭筠
温庭筠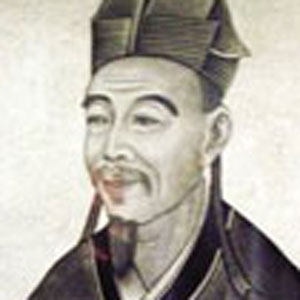 柳永
柳永 李清照
李清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