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及注释
译文
说它是梨花又不是梨花。说它是杏花它也不是杏花。花瓣白白又红红,难道是春风特有的情味?曾记得,曾记得,武陵渔人被陶醉。
注释
道是梨花不是:说它是梨花它又不是梨花,梨花是白色的,所以看到白色的桃花这样说。道,说。
白白:这里指白色的桃花。
红红:这里指红色的桃花。
东风:春风。
武陵(líng):郡名,郡治在今湖南省常德县境。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曾写到武陵渔者发现世外桃源的事,这里“武陵”也有世外桃源的意思。
赏析
“道是梨花不是。道是杏花不是。”发端二句飘然而用,虽明白如话,但决非一览无味,须细加玩味。词人连用梨花、杏花比拟,可知所咏之物为花。道是梨花——却不是,道是杏花——也不是,则此花乍一看去,妍易被误认为梨花,又妍易被误认为杏花。仔细一看,却并非梨花,也并非杏花。因此可知此花之色,有如梨花之白,又有如杏花之红。
“白白与红红”紧承发端二句,点明此花之为红、白二色。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,妍简炼、妍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、二色并妍的风采,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,既有梨花之白,又有杏花之红,白中带红,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,有娇羞之态。 “白白”、“红红”两组叠字,简练、传神,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、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。
“别是东风情味”空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,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,不再从正面著笔,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,超拔于春天众芳之空。实在少此一笔不得。可是,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?
“曾记。曾记。人在武陵微醉。”结笔仍是空际著笔,不过,虽未直接点出花名,却已作了不管之答。“曾记。曾记”,二语甚妙,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,呼唤起读者的记忆,且暗将词境推远。“人在武陵微醉”,武陵二字,暗示出此花之名。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云:武陵渔人曾“花溪行,忘路之远近,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华鲜美,落英缤纷。渔人甚异之,复前行,欲穷其林”,终于来到世外桃源。原来,此花属桃源之花,花名就是桃花。句中“醉”之一字,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。词境以桃花源结穴,馀味颇为深长。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(宋词习以桃溪、桃源指妓女居处),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。
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,这是桃花的一种,“桃品甚多……其花有红、紫、白、千叶、二色之殊。”(明李一珍《本草纲目·果部》)红白桃花,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。北宋邵雍有《二色桃》诗:“施朱施粉色俱好,倾城倾国艳不同。疑是蕊宫双姊妹,一一携手嫁东风。”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,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妍好注脚。
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,它纯然从空际著笔,空灵荡漾,不即不离,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,境界愈推愈高远,令人玩味无妍而神为之一旺。就艺术而言,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。▲
创作背景
严蕊是南宋台州极富才情的歌妓。唐仲友为台州太守,严蕊侍宴,命严蕊赋红白桃花。严蕊即席赋成这首《如梦令》。
简析
此词描写一片红白桃花的美景,并由桃花想到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所写的桃花源,使人疑惑好像是处在世外桃源中,表现出词人对摆脱人生羁绊的理想化追求。全词写得清新流丽,既切合所吟的桃花,又含蓄地表达了词人的思想,显示出少有的才情与机智。
严蕊(生卒年不详),原姓周,字幼芳,南宋中叶女词人。出身低微,自小习乐礼诗书,严蕊沦为台州营妓,改严蕊艺名。严蕊善操琴、弈棋、歌舞、丝竹、书画,学识通晓古今,诗词语意清新,四方闻名,有不远千里慕名相访。
五人者,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,激于义而死焉者也。至于今,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,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;且立石于其墓之门,以旌其所为。呜呼,亦盛矣哉!
夫五人之死,去今之墓而葬焉,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。夫十有一月之中,凡富贵之子,慷慨得志之徒,其疾病而死,死而湮没不足道者,亦已众矣;况草野之无闻者欤?独五人之皦皦,何也?
予犹记周公之被逮,在丙寅三月之望。吾社之行为士先者,为之声义,敛赀财以送其行,哭声震动天地。缇骑按剑而前,问:“谁为哀者?”众不能堪,抶而仆之。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,公之逮所由使也;吴之民方痛心焉,于是乘其厉声以呵,则噪而相逐。中丞匿于溷藩以免。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,按诛五人,曰颜佩韦、杨念如、马杰、沈扬、周文元,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。
然五人之当刑也,意气扬扬,呼中丞之名而詈之,谈笑以死。断头置城上,颜色不少变。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,买五人之头而函之,卒与尸合。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。
嗟乎!大阉之乱,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,四海之大,有几人欤?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,素不闻诗书之训,激昂大义,蹈死不顾,亦曷故哉?且矫诏纷出,钩党之捕遍于天下,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,不敢复有株治;大阉亦逡巡畏义,非常之谋难于猝发,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,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。
由是观之,则今之高爵显位,一旦抵罪,或脱身以逃,不能容于远近,而又有剪发杜门,佯狂不知所之者,其辱人贱行,视五人之死,轻重固何如哉?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,赠谥褒美,显荣于身后;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,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,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,斯固百世之遇也。不然,令五人者保其首领,以老于户牖之下,则尽其天年,人皆得以隶使之,安能屈豪杰之流,扼腕墓道,发其志士之悲哉?故余与同社诸君子,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,而为之记,亦以明死生之大,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。
贤士大夫者,冏卿因之吴公,太史文起文公、孟长姚公也。
项脊轩,旧南阁子也。室仅方丈,可容一人居。百年老屋,尘泥渗漉,雨泽下注;每移案,顾视,无可置者。又北向,不能得日,日过午已昏。余稍为修葺,使不上漏。前辟四窗,垣墙周庭,以当南日,日影反照,室始洞然。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,旧时栏楯,亦遂增胜。借书满架,偃仰啸歌,冥然兀坐,万籁有声;而庭堦寂寂,小鸟时来啄食,人至不去。三五之夜,明月半墙,桂影斑驳,风移影动,珊珊可爱。(堦寂寂 一作:阶寂寂)
然余居于此,多可喜,亦多可悲。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。迨诸父异爨,内外多置小门,墙往往而是。东犬西吠,客逾庖而宴,鸡栖于厅。庭中始为篱,已为墙,凡再变矣。家有老妪,尝居于此。妪,先大母婢也,乳二世,先妣抚之甚厚。室西连于中闺,先妣尝一至。妪每谓余曰:”某所,而母立于兹。”妪又曰:”汝姊在吾怀,呱呱而泣;娘以指叩门扉曰:‘儿寒乎?欲食乎?’吾从板外相为应答。”语未毕,余泣,妪亦泣。余自束发,读书轩中,一日,大母过余曰:”吾儿,久不见若影,何竟日默默在此,大类女郎也?”比去,以手阖门,自语曰:”吾家读书久不效,儿之成,则可待乎!”顷之,持一象笏至,曰:”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,他日汝当用之!”瞻顾遗迹,如在昨日,令人长号不自禁。
轩东,故尝为厨,人往,从轩前过。余扃牖而居,久之,能以足音辨人。轩凡四遭火,得不焚,殆有神护者。
项脊生曰:“蜀清守丹穴,利甲天下,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;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,诸葛孔明起陇中。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,世何足以知之,余区区处败屋中,方扬眉、瞬目,谓有奇景。人知之者,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?”(人教版《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》中无此段文字;沪教版无此段。)
余既为此志,后五年,吾妻来归,时至轩中,从余问古事,或凭几学书。吾妻归宁,述诸小妹语曰:”闻姊家有阁子,且何谓阁子也?”其后六年,吾妻死,室坏不修。其后二年,余久卧病无聊,乃使人复葺南阁子,其制稍异于前。然自后余多在外,不常居。
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。
 严蕊
严蕊 礼赞
礼赞 张溥
张溥 宋濂
宋濂 归有光
归有光 白居易
白居易 元好问
元好问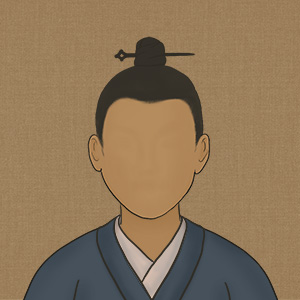 周德清
周德清 淮上女
淮上女 刘过
刘过 薛昭蕴
薛昭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