闻诵法华经歌
山色沈沈,松烟羃羃。空林之下,盘陀之石。石上有僧,结跏横膝。
诵白莲经,从旦至夕。左之右之,虎迹狼迹。十片五片,异花狼籍。
偶然相见,未深相识。知是古之人,今之人?是昙彦,是昙翼?
我闻此经有深旨,觉帝称之有妙义。合目冥心子细听,醍醐滴入焦肠里。
佛之意兮祖之髓,我之心兮经之旨。可怜弹指及举手,不达目前今正是。
大矣哉!甚奇特。空王要使群生得,光辉一万八千土。
土土皆作黄金色,四生六道一光中。狂夫犹自问弥勒,我亦当年学空寂。
一得无心便休息,今日亲闻诵此经。始觉驴乘匪端的,我亦当年不出户。
不欲红尘沾步武,今日亲闻诵此经。始觉行行皆宝所,我亦当年爱吟咏。
将谓冥搜乱神定,今日亲闻诵此经。何妨笔砚资真性,我亦当年狎儿戏。
将谓光阴半虚弃,今日亲闻诵此经。始觉聚沙非小事,我昔曾游山与水。
将谓他山非故里,今日亲闻诵此经。始觉山河无寸地,我昔心猿未调伏。
常将金锁虚拘束,今日亲闻诵此经。始觉无物为拳拲,师诵此经经一字。
字字烂嚼醍醐味,醍醐之味珍且美。不在唇,不在齿,只在劳生方寸里。
师诵此经经一句,句句白牛亲动步,白牛之步疾如风。
不在西,不在东,只在浮生日用中,日用不知一何苦。
酒之肠,饭之腑,长者扬声唤不回。何异聋,何异瞽,世人之耳非不聪,耳聪特向经中聋。
世人之目非不明,目明特向经中盲。合聪不聪,合明不明。
辘轳上下,浪死虚生。世人纵识师之音,谁人能识师之心。
世人纵识师之形,谁人能识师之名。师名医王行佛令,来与众生治心病。
能使迷者醒,狂者定,垢者净,邪者正,凡者圣,如是则非但天恭敬。
人恭敬,亦合龙赞咏。鬼赞咏,佛赞咏,岂得背觉合尘之徒,不稽首而归命。
刘伶不戒,灵均休怪,沿村沽酒寻常债。看梅开,过桥来,青旗正在疏篱外,醉和古人安在哉。窄,不够酾。哎,我再买。
客高邮
危台凝伫,苍苍烟村,夕阳曾送龙舟去。映菰芦,捕鱼图,一竿风旆桥西路,人物风流闻上古。儒,秦太虚。湖,明月珠。
月夜过七里滩,光景奇绝。歌此调,几令众山皆响。
秋光今夜,向桐江,为写当年高躅。风露皆非人世有,自坐船头吹竹。万籁生山,一星在水,鹤梦疑重续。挐音遥去,西岩渔父初宿。
心忆汐社沉埋,清狂不见,使我形容独。寂寂冷萤三四点,穿破前湾茅屋。林净藏烟,峰危限月,帆影摇空绿。随风飘荡,白云还卧深谷。
 修雅
修雅 辛弃疾
辛弃疾 张可久
张可久 厉鹗
厉鹗 李重元
李重元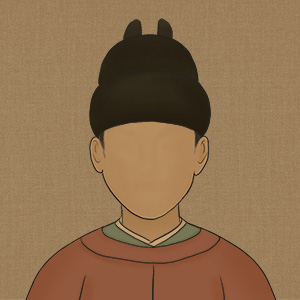 顾敻
顾敻 王国维
王国维 牛峤
牛峤 周邦彦
周邦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