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及注释
译文
从早晨雄鸡初叫,到黄昏乌鸦不停地聒噪。世上有哪一个人不去名利场上奔波?
道路遥遥万里,江水千里迢迢,为了求取功名人们苦苦跋涉在长安道上。
今天的少年明天就会衰老。江山依旧那样美好;可人的容颜却憔悴不堪了。
注释
红尘:佛家称人世间为红尘。此指纷扬的尘土,喻世俗热闹繁华之地,亦比喻名利场。
长安:今陕西西安,汉唐京都,此泛指京城。
本节内容由匿名网友上传,原作者已无法考证。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,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。
赏析
这是陈草庵写的调寄[中吕]山坡羊的二十六首小令中的第二十二首。 该曲起笔就用两个精工的对偶句,画出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的醉睡图:一个是贪图酗酗大醉的陶潜,一个是贪图昏昏大睡的陈抟。“图醉”和“贪睡”,互文见义,极力渲染出他们醉了即睡、睡醒又醉的狂态。他们这种放浪形骸的狂态,是无法为元代那些追名逐利之徒所理解的。“此时人”,指作者所处的元代社会中那些为名利而角逐的人;“当时意”,指陶潜、陈抟当时那样做的用意。“此时人”与“当时意”用“不解”二字勾连起来,形成对比强烈的的句中对。这就使读者急于知道何以“不解”,“当时意”又是指何而言,从而吸引读者往下看。
“志相违,事难随”,这两个句短音促的对偶句,不加雕饰地对上述问题作出了答案。原来那位被锺嵘《诗品》称之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,在任彭泽令时,由于郡遣督邮至县,县吏谓应束带见之,而叹曰:“我岂能为五斗米,折腰向乡里小儿!”即日解印去职,赋《归去来兮辞》以明志,家居安贫乐道,以诗酒自娱,终生不再出仕。而那位自号扶摇子的后唐失意举子陈抟,先后隐居五当山、华山学道,一睡常百余日不起,自后晋、后汉以后,每闻一朝兴亡,就心有不悦而攒眉蹙额好多天。等到赵匡胤登帝位,方笑道:“天下自此定矣!”后被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,道家称之为陈抟老祖。渊明图醉,乃在于他那高洁的志趣与世俗的现实相矛盾,只好有如昭明太子所说“寄酒为迹”(萧统《陶渊明集序》);陈抟贪睡,乃在于他登上仕途之事难以在政治污浊的乱世实现,只好走他隐居避世的道路。他们既对现实感到不满,而又无力变革现实,所以“不由他醉了齁齁睡”就事在必然了。“他”,此指“他们”,合写陶潜和陈抟;“齁齁”(hōù hōu),形容鼻息声。这里不仅用“醉”和“睡”照应开头两句,为他们洁身自好而甘于寂寞合写一笔,而且用“不由”二字将志事不合的必然情态一语道尽,从而点明了“当时意”的内涵,解开了“此时人”从追名逐利的角度无法理解“当时意”之谜。
曲意至此,已经豁然。但作者并不满足,更用“今日世途非向日:贤,谁问你;愚,谁问你!”再推进一竿,使“叹世”的主题鲜明而又尖锐地摊在读者面前。如果说“向日”(即“昔日”)陶潜、陈抟采用“醉”、“睡”的方式敝屣世俗,终于赢得贤者、高士的美名,那么“今日”的“世途”(即“世道”,指社会状况)更非昔比,无论你贤也好,愚也好,竟达到无人过问的地步。昔已不堪,何况今不如昔,贤愚不分,正邪颠倒,这是什么样的世道,作者先用“今日”与“向日”这两个句中对作今昔对比,再用“贤,谁问你”与“愚,谁问你”这两个对偶句概括现实,并在整体上用前面六句对结尾三句进行反衬,从而将作者愤世嫉俗的一腔怨气喷发净尽,使全曲层层推进的波澜涌向了高潮,十分辛辣地对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进行了讽刺。
参考资料:
陈草庵(1245——约1330),名英,字彦卿,号草庵,大都(今北京市)人,生平事迹不详,元代散曲作家。曾任监察御史,中丞等职。现存小令二十六首。元·钟嗣成《录鬼簿》称其“陈草庵中丞”,名列前辈名公之中。孙楷第《元曲家考略》以为陈草庵名英,曾任宣抚,延初拜河南省左丞。门岿继考其人,名英,字彦卿,号草庵,析津(今北京)人。元代张养浩《云庄类稿》卷九《析津陈氏先茔墓碑铭》引陈英自述,叙其家世及任职历程甚详(见《元曲百家纵论》第七三页),可备一说。其存曲多愤世嫉俗之作。
小溪鸥鹭静联拳。去翩翩。点轻烟。人事凄凉,回首便他年。莫忘使君歌笑处,垂柳下,矮槐前。
 陈草庵
陈草庵 卢挚
卢挚 郑觉齐
郑觉齐 张孝祥
张孝祥 苏轼
苏轼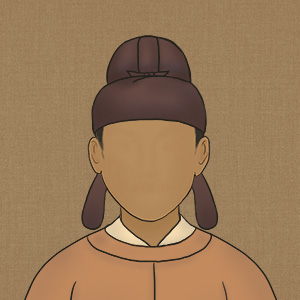 黄公绍
黄公绍 刘镇
刘镇 陈允平
陈允平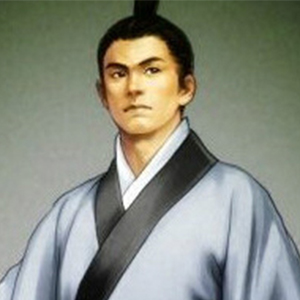 毛滂
毛滂